作为慈善事业与金融工具结合的创新形态,慈善信托的透明度直接关系到公众信任、资金安全与公益目标的落地。近年来,随着慈善法修订、“慈善中国”平台推广及行业实践深化,我国慈善信托信息披露体系逐步成型,但在执行层面仍面临“披露不均、质量参差、监管待强”等现实挑战。
截至记者发稿时,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慈善中国”共有2538条慈善信托备案信息,财产总规模共计972446.69万元。制度与市场的磨合仍在进行,但公众对透明与信任的期待,已然成为慈善信托发展的最大压力与动力。
披露率与质量的“两极分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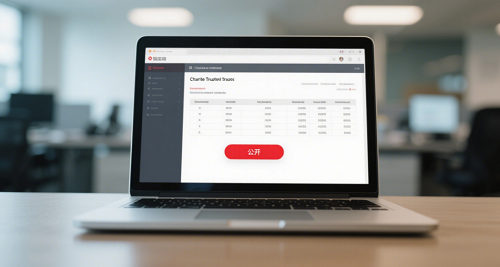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落地,慈善信托作为新型制度被寄予厚望。然而9年过去,透明度问题依然成为焦点。记者通过“慈善中国”或部分信托机构官网发现,社会公众能获取的披露信息,往往仅限于备案数量和信托期限等基础数据。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进展、以及是否独立审计,大多数公众无从得知。
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相对走在前列,建立了年度报告制度,并引入了第三方审计,但全国并未形成统一的披露框架。部分信托公司在民政部门网站上公布年报,部分只保留“备案信息”,还有的几乎没有后续信息更新,这种“拼图式”的公开方式,使公众难以形成完整认知。
在全国较早试点慈善信托信息披露的地方——北京,记者通过北京市民政局官网输入慈善信托关键词“备案”“终止”等信息检索,虽然能跳出众多有关此项慈善信托的信息,但检索单个信托项目依然有难度。县域层面的慈善信托问题更明显,部分项目仅通过地方民政部门官网发布简单通知,无财务报表、无项目照片,公众难以判断公益实效。
同时,技术应用与资源投入的“冷热不均”也加剧着慈善信托的信息披露差距。一些头部信托公司凭借资金优势,投入数百万元开发数字化披露系统,但中小机构(尤其是县域慈善组织担任受托人的项目)受限于成本,只能依赖“Word文档+官网附件”的传统方式,导致信息查询分散、格式不统一。
北京某信托机构家族办公室分析师刘敏表示,部分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存在“选择性披露”,要么仅公开项目名称、委托人信息等基础内容,对“资金具体用途、受益人筛选标准、管理费用计算方式”等关键信息避而不谈;要么披露内容滞后,失去信息的时效性。仅有少部分信托项目达到“数据完整、逻辑清晰”的标准。
慈善信托的核心价值,在于以“信托财产独立性”保障公益目标的长期实现,而信息披露则是维系公众信任、确保公益初心不偏离。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慈善研究中心高级政策分析师尹力子认为,在公众眼中,“慈善”和“信托”都属小众概念,两者结合形式更为复杂。这种认知壁垒,使得慈善信托信息披露存在不足,影响公众信任也制约行业发展。
信披处罚偏低难以震慑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未按规定披露信息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但实践中,全国因信息披露问题被处罚的案例不多,且多为“限期改正”的轻微处理,难以形成震慑。
2023年10月20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西监管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对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罚款72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查明主要违法违规事实中有一项涉及“违规开展慈善信托业务”。其后,该机构只是被民政部门约谈,这让行业对违规的重视程度不足。
尹力子表示,民政部门与信托公司的关系比较微妙,它不是信托公司的业务主管部门,只是公司开展的慈善信托业务受它的监管。民政部门可以监管慈善信托,但对于直接处罚信托公司受托人较为谨慎,也需要和金融监管部门协调。
此外,民政、金融监管、税务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尚未打通,部分信托通过“关联交易”规避披露。例如,受托人将信托资金投资于关联企业,却未在报告中说明关联关系,而金融监管部门的投资备案信息与民政部门的披露信息未联网,难以发现此类问题。
尹力子认为,其披露信息散落在地方民政官网、受托人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且年度报告与项目进展未分类,公众需逐页查找才能获取关键数据;更有部分项目因缺乏技术支持,未及时更新信托财产变更信息(如股权分红到账情况),这有可能引发公众质疑。
另外,税收政策模糊也进一步抑制披露积极性。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明确慈善信托可享受税收优惠,但具体操作细则(如非上市公司股权估值抵税、信托财产增值部分免税)仍未明确。部分委托人因担心“披露资产细节后,税务部门对抵税额度提出异议”,遂选择简化披露内容。
刘敏举例说,某家族设立的“教育慈善信托”,持有多家非上市公司股权,但年报中仅披露“股权市值约5000万元”,未说明估值方法与企业经营状况,委托人就坦言,怕详细披露后,税务部门不认可抵税金额,反而增加麻烦,干脆简化披露。
2025年7月7日,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在举行的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在慈善事业促进方面,将加快健全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慈善信托等慈善法配套制度。
渠道与标准正在统一
尽管有着诸多挑战,但信息披露的渠道与标准正在逐步统一。
我国慈善信托信息披露的制度体系,已形成以法律为核心、部门规章为支撑、地方细则为补充的多层级架构,为透明化运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首次将慈善信托纳入规制范围,明确“受托人应当向民政部门报告信托事务处理情况及财务状况,并向社会公开”。2023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进一步强化义务,要求受托人对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负责,并新增“民政部门建立慈善信托信用记录”的条款,将披露表现与信用挂钩。
2025年1月施行的《慈善信托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规定》则更细化,明确年度报告需包含“支出明细、管理费用占比、项目执行进度”等核心数据,避免“模糊披露”。
根据《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慈善中国”平台成为全国慈善信托信息披露的核心载体,受托人需在此公示信托设立说明、年度报告、变更终止事由等信息;同时,各地民政部门(如北京、上海、广州)也在官网开设专栏,补充披露本地备案信托的细节,部分地区还探索了“标准化模板”。
同时,监管与评估机制也在创新试点。
 广州市出台《慈善信托评估指引(试行)》引入第三方评估
广州市出台《慈善信托评估指引(试行)》引入第三方评估
2020年11月,广州市出台《慈善信托评估指引(试行)》,明确了评估原则、对象和内容、组织和职责、评估程序、其他事项等。慈善信托评估内容包括“慈善信托的规范管理”“慈善目的的实现”“慈善信托的运用效益”“综合评价”等四个指标共100分。
广州引入第三方机构(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对信托的“信息披露完整性、资金使用合规性”进行量化评分,评估结果分为 A(优秀)、B(合格)、C(待改进)三级,为公众选择信托项目提供参考。
透明度与技术的双重突破
随着制度落地与行业重视,我国慈善信托信息披露的实践成效逐步显现,尤其在覆盖面、技术应用与公众参与方面,呈现出积极变化。从披露覆盖面来看,头部机构与大额信托的透明度显著提升。
 “顺德社区慈善信托”在和的慈善基金会官网显示
“顺德社区慈善信托”在和的慈善基金会官网显示
以中信信托管理的“中信·何享健慈善基金会2017顺德社区慈善信托”(规模超4.9亿元)为例,记者在和的慈善基金会官网上看到,其不仅每年在官网发布慈善信托年报,还详细解读资金使用情况;万向信托的“碳中和公益慈善信托”则按月在官网更新项目进展,包括植树面积、碳减排量等具体数据,让公众直观感受公益成效。
技术创新进一步打破了“信息壁垒”。部分机构开始探索“区块链+慈善信托”模式,实现资金流向可追溯、信息不可篡改。
记者注意到,2023年,浙商银行在本省内试点启动“善本信托工程”,该行杭州分行为助力临平人民医院医疗救助基金设立的“善本信托˙浙金-圣兆慈善信托”,就将每笔项目拨款记录上链,公众通过官网扫码即可查询资金从信托账户到受益人的全路径。
与此同时,公众参与渠道也在拓展。
除官方平台外,慈善信托信息披露正逐步融入ESG(环境、社会、治理)评价体系。
2024年,“杭州上市公司ESG战略慈善影响力排行榜”将“信息透明度”纳入核心指标,权重占比达20%,推动企业将慈善信托披露作为社会责任管理的重要环节。比如,浙商银行就将该行的善标、善本信托全方位地进行慈善信息披露。
尽管我国慈善信托信息披露面临披露不均、技术不足等挑战,但制度完善、技术创新与监管强化的趋势已明确。随着“标准统一、技术驱动、监管协同”的透明生态逐步成型,慈善信托将真正实现“阳光下运行”。
“慈善信托最大的问题,不是制度设计,而是社会理解。”尹力子表示,要统一全国披露标准,让公众能清晰追踪资金流向。加强社会认知推广,让慈善信托成为公众信赖的公益模式。




